我喜欢用玻璃杯泡茶,看那杯中的风景――微波涟漪像轻风掠水,浊中透清似深潭倒影,绿叶上下翻卷如龙蛇摆尾,青�左右摇曳若�娥舞缦――一杯茶,一幅水彩画。
轻轻吹开浮梗,小心地啜上一口,让它在舌尖上停留一会儿,慢慢沿着喉咙滚下去,倒吸气,咂咂嘴巴,丝丝带有糯、醇、苦、涩的清香就在肺腑中回荡!
苦涩也在这个夏天回荡,莫名的烦恼会突然而至,溽热的焦虑也会袭来,倦怠和无趣在空气中弥漫,只有那杯绿茶给我带来些许慰藉,我用食指和拇指夹着杯沿儿轻轻摇晃,思绪渐渐地摆脱了烦恼和焦虑,儿时的一幕浮现出来......
上小学的时候我家随着父亲的单位从大连搬到宽甸县城北郊外,住在一个家属大院里。没有院墙的大院和县城不挨着,和村庄也不挨着,像孤岛一样伫立在田林中。我家的房子在最后一排,屋后是种着玉米的农田,稍远处就是著名的小娘娘沟,再往远看可见山峦起伏,林木葱茏,那是长白山脉的延续。
那片玉米地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就是一片森林。放暑假了,我钻进了“森林”,走着走着,只能抬头看到天,却找不到出去的路了。我像无头苍蝇一样撞来撞去,胳膊和小腿被玉米叶子划出一道道血痕,心里害怕起来。怎么办?我定定了神,一下子想起老师讲的故事《汤姆历险记》汤姆在岩洞里迷路的情节,汤姆能出去,我也能出去,我决定朝一个方向走,一直走,不回头,居然就这样不知从何处走了出来。
眼前出现一座破败的茅屋,一个蓬头垢面,破衣烂衫的孩子站在那里好奇地看着我,他没有说话。
我主动搭话:“这是你家吗?”
他点了点头。
“那边好玩吗?”我指了指长满花草的后山坡。
他又点了点头。
“那你带我去玩好不好?”
他还是点了点头。
一起在山坡玩了很长时间,他渐渐地放开了神态,有了孩童该有的笑容,也有话了。捉住螳螂后,他教我掐着它的长脖子任由它张牙舞爪。把它放掉吧,我想起了老师讲过螳螂是益虫。三彪子把装着蛐蛐的小笼子给了我,看着蛐蛐委屈地叫着,我也想放了它。但是蚂蚱就不一样了,我学着蚂蚱的样子跳着扑向蚂蚱,也追着蝴蝶、捉蜻蜓。不知道现在孩子还能不能体会到那种简单朴素的快乐,在那个没有电子设备的时代,这就是一场游戏的盛宴。
太阳下山了,远远的,我听到了妈妈用浓重的山西口音拉着长调喊我:“国仔――回家吃饭了――”
只知道这个孩子的诨名叫三彪子,不知道为什么给他起这个不雅的外号。他应该排行老三,也不“彪”。我约了三彪子去我家玩,他不置可否。其实两家离得并不远,除了隔着一片玉米地,还有一片小树林,但是像隔着一个世界。
第二天,我在后窗户看见三彪子在玉米地边儿上向我家张望,我大声喊他,他怯生生地站在那里不动,我只好出去找他。这一切都被我妈妈看到了,和这么一个蓬头垢面,衣着褴褛的小孩玩,妈妈似乎有点儿吃惊,但是她没有说什么。我领着三彪子在我家的前后院子里乱转,可他怎么也不进我家门。他要回家了,妈妈却叫住了他,把一包我穿过的却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塞给了三彪子。
三彪子后来经常找我玩,每一次都是在玉米地向我家张望,每一次都不进家门,每一次母亲不是给他穿的就是给他吃的,让他带回家。
俗话说的“老西子”一是爱吃醋,二是“抠”。妈妈省吃俭用是出了名的,什么都不舍得给外人,可是对这个穷孩子却大方出手,这件事情对我一生影响很大。
那年的夏天过去了,我回到学校住校了,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三彪子。
每当想起这个孩子,心都惶惶然。后来和弟弟妹妹谈起此事,他们竟然都知道三彪子,也都记得我和三彪子一起玩的那段往事。这么点小事能有这么深的共同记忆,实际上都是源于妈妈的善良。
茶杯里面隐约地浮现出妈妈的影像,她还是那么年轻。天上一日,地上一年,她也就离开我们一个多月了吧。人的记忆是复杂的,总是排除不那么重要的,留下刻骨铭心的。我只想留下善良。
庚子年,又是一个苦夏。
(文/檐马玎当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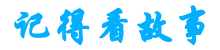


支付宝转账赞助
支付宝扫一扫赞助
微信转账赞助
微信扫一扫赞助